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”是国人对自闭症很诗意的表述。
在美国也有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概念:“困在躯壳里的孩子”。 这个概念认为“真正的”孩子们藏在患有自闭症的身体外壳之下。虽然列昂·肯纳教授(诊断第一例孤独症者的医生)本人没有使用过这种说法,但他曾经让人们注意他治疗的那 11 个孩子的表情,这无意间激起了人们的这种想法。

肯纳医生曾提到“ 严肃的思考”“ 华丽的表达”以及“ 优秀的认知能力”等内容,并表示这些“毫无疑问,都是天生的”。
当自闭症患儿可以不被打扰,游荡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,他们就会感到满足,嘴角会浮现出一抹“平和的微笑”。肯纳描写他看到的这种“平和的微笑”时,就好像在思考这些孩子真正的身份,或者说,他们如果不再被自闭症限制,将成为什么样子。
这种想法具有无比强大的传播力,自闭症患儿的父母甚至经常梦见它。
“再大一点,孩子会说话了就好了。”
在回忆录、网上论坛和与自闭症患儿父母的谈话中,虽然有时措辞不同,但这种说法总是会出现。
这些父母徘徊在希望与痛苦之间,而正是“解放”他们孩子的可能性让他们充满希望。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,他们就会充满负罪感,认定自己为孩子做得还不够多。这就好像自闭症是一个上了锁的房间,而他们一直在寻找钥匙一样。
从许多方面来看,只有受自闭症困扰的家庭有着强烈的找到“困在身体里的孩子”的欲望。
对于患有其他发育病症,比如唐氏综合征的家庭来说,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是接受孩子现在的样子, 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,但并不期待病情会有根本性的好转。
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同样爱他们的孩子,但其中很多人总想“拯救”自己的孩子,并希望找到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来达到这一目的。 对于刚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来说,他们的父母尤其如此。因为这些儿童大部分还不到 6 岁,而几乎所有专家都认同的一点是,要在自闭症患者 6 岁前对其进行强化治疗。这些父母甚至不想接近那些更有经验的父母,因为那些人会告诉自己不要抱有太大希望。

他们也不喜欢科学家们提出的对采用流行疗法的警告:科学家们认为这些疗法缺乏实证支持。
因为时间紧迫,而他们的孩子需要救助,这些刚接触自闭症的父母决定无视这些警告。他们认为,只要这些疗法看起来合理并不会伤害到任何人,做出尝试无疑比什么都不做更好。
于是,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每一个 10 年,父母们都在尝试各种替代疗法,而这些疗法你方唱罢我登场,有时会引发轰动,但通常在轰动之后又会带来失望。

2010年摄影师郑敏拍摄照片,因为无法阻止孩子的自伤行为,这位名叫菲菲的孤独症女孩被送进医院进行了脑部手术(我猜测是大脑干细胞移植),家里花了很多钱,孩子吃了不少苦,术后9个月一切回到了原点。这些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疗法充斥着各种正规的医院和机构。
在国外也不例外,让我们来看看各种奇葩疗法!
在南非,人们将稀释后的漂白剂兑在灌肠剂中,希望通过给儿童灌肠的方式让他们摆脱身体内的恶魔;
在别的地方,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来杀死自闭症导致的“细菌”。
父母们还报名参加了“拥抱治疗”——一种由纽约精神病专家玛莎·韦尔奇(Martha Welch)推进,并受到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鸟类学家支持的疗法。该疗法要求母亲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并冲他们喊叫,直到他们迈出通向治愈之路的第一步——打破无声状态。
在法国,父母们尝试了“打包疗法”,该方法将儿童像蚕一样紧紧包裹在潮湿的、被冰过的床单中,只露出头来。
其他方法还包括大剂量维生素疗法、特殊饮食法以及亲近海豚和马的动物疗法。
所有这些方法都来自看似合理的理论,并总有来自父母的报告指出,某一种方法至少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效果。这些疗法的流行常常是通过父母间的口耳相传,但有的疗法也得到了媒体的大面积宣传。
这样的事就于 1993 年发生在了维多利亚·贝克身上。她是一名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母亲。当时,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帕克不再受长期肠胃疼痛的折磨,她带着他跋涉 500 英里来到马里兰州的一家研究医院。作为诊断性测试的一部分,医生给患有自闭症的帕克注射了一种从猪身上提取、名叫“促胰液素”(secretin)的激素,之后几天,他的消化系统功能、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,于是贝克将这件事告知了媒体。新闻播出后,促胰液素的需求量开始急剧上升。在一些地区,制作成本不到 180 美元的 4 针药卖到了 8000 美元。但在临床实验中,这种药却再也没有产生过对帕克的那种效果了。
与促胰液素实验一样,其他各种疗法在接受关于其有效性的科学测试时,也都没能通过。大多数尝试了这些疗法的父母都失望而归。有了类似经历后,很多父母明白了,他们不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追逐这些最新的“奇迹疗法”上。
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觉悟。很多确定无效的替代疗法依然在聚光灯之外不定期活跃着,坚持使用这些疗法的父母最多只会表示自己孩子的症状有了改善。没有人能绝对否认,在很小的群体中可能确实出现过,或看似出现过真正的临床上的症状改善。而对于依然使用这些疗法的父母,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们没尽力去解救那个被困在身体里的孩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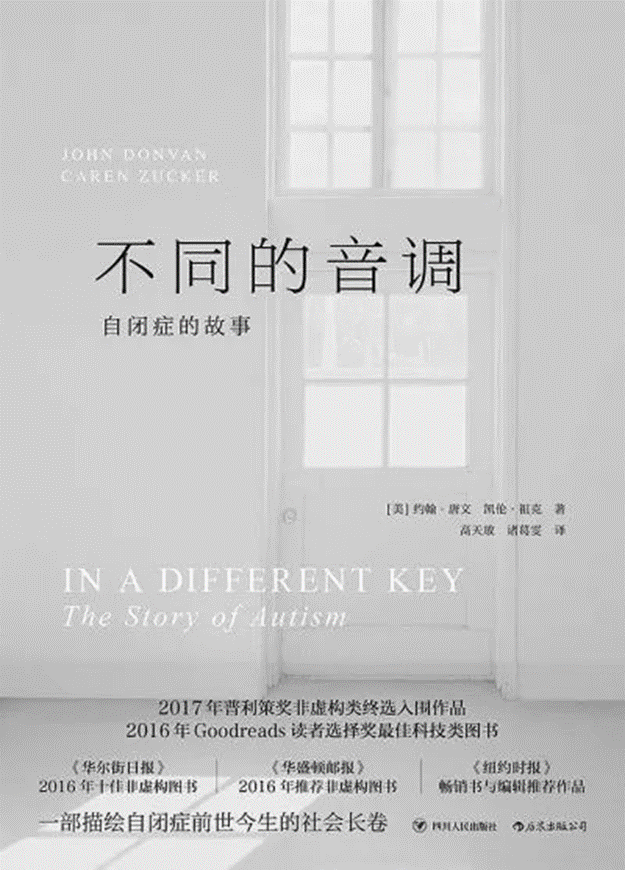
本文来自后浪出版社出版的《不同的音调》一书
